主讲人:孔祥毅
随着山西商品经营资本的发展,逐渐从中分离出来了一种货币经营资本,先后有当铺、钱庄、印局、票号、账庄等几类金融企业,遍布全国各地乃至亚欧一些国家。外国人把这些金融机构统称“山西银行”。有的山西金融机构在国外注册名称就叫银行,如山西祁县合盛元票号在日本、朝鲜挂牌就是“合盛元银行”。据1909年日本出版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编写的《天津志》记载:“汇票庄俗称票庄,总称是山西银行。据说在一百多年以前业已成立。主要从事中国国内的汇兑交易,执行地方银行的事务。”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伟大的的革命》一书中说:“在外国人来到以前,在最上层信贷的转让,是由钱庄经手,这些钱庄集中于山西中部汾河流域的一些小镇。山西银行常常靠亲属关系在全国设立分号,把款子从一个地方转给其他地方的分号,为此收取一些汇水”。“在上层和低层之间还有几类大大小小的外国人称为地方银行的钱庄。小钱庄可以服务于它们所在地的社区,大的钱庄则常和分布在通都大邑的地方银号有往来。”
德国学者李希霍芬[1](1833-1905),在1868-1872年间,七次在中国旅行,著有《中国》三卷。李希霍芬多次到山西考察,他说:“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当时居于领导地位的金融机关——山西票号,掌握着全中国,支配着金融市场,可以说计算的智能劳动是该省的唯一输出的商品,这也是财富不断流入该省的原因。这种财源也受到鸦片的极大损害。在所有中国人中,对中国特有的尺度、数、度量观念以及基于这种观念的金融业倾向最发达的要数山西、陕西两地的人,作为最古老文化的保持者,他们获得了邻人或周围国家居民的精神上的优越感,保持了这种优越感的种族,即使在其后代丧失了政治势力以后也能通过发达的数量意识和金融才华显示精神优越的成果来。这种在西南亚洲明显出现的现象,在此地又出现了。山西人作为最古老文化的保持者,他们的优越感能以其他形式继续下去。” 外国人之如此高度评价山西银行,是因为山西银行挈领了中国金融革命。
一、机构与工具创新
近百年来,很多人都知道山西商人经营的票号,并给了应有的历史评价。岂不知山西商人经营的当铺、钱庄、银号、印局、帐局,在中国明清直到民国时期有着同样的重要地位,但由于下列原因却被人们忽视了:(1)票号资本较多,一般在100000-500000两白银左右,而当铺、印局、帐局、钱相对资本较小,一般在500-50000两之间;(2)票号分支机构多,遍布全国各大城市和重要商埠码头,而当铺、印局、帐局、钱庄设置分支机构相对较少,故影响较小。(3)票号客户多是大商人、大官吏和政府,业务数额巨大,很少与小商号和小生产者往来,而当铺、印局、帐局、钱庄的客户对象主要是小生产者和普通商户,虽然也有一些大客户,但毕竟以中、小业务为主。票号多交结达官贵人,气势较大,而当铺、印局、帐局、钱庄很难交结王公大臣。⑷ 从历史发展看,当铺、印局、帐局、钱庄早于票号,衰亡又晚于票号,历史寿命比票号长。按资本总额计算,由于当铺、印局、帐局、钱庄家数多,总资本并不比票号少。按活动地域,山西的当铺、印局、帐局、钱庄遍设全国各地,不论京都闹市,还是边远乡村,就是在国际舞台上,它们也不比票号的活动少。可惜,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尚未完成,还有待今后予以补充。这里只作一大略介绍。
中国的金融机构产生最早的是典当,早在南北朝时已经出现。明朝又出现了钱庄,后来还有银号,其业务经营和利润导向与钱庄相同,只是名称不同,江浙人多称钱庄,京津人多称银号。但是到了清康熙以后,适应中国商品经济发展需要,金融机构得到了迅速发展,不仅当铺、钱庄遍布全国城市集镇以至农村,而且又出现了印局、账局、票号等金融机构。这些土生土长的中国式金融机构,最初都是单一的金融业务,通过不断的创新金融工具、创新金融业务、创新金融技术、创新金融制度,向着存款、放款、兑换、汇兑、代理、代办、委托等综合发展。它们是中国银行业的先驱。
典当
典当业,也称当质业,是最古老的金融业,历史上名称比较多,有质库、质肆、质店、解库、长生库、解典库、典库、抵当库等等,按照资本数量与经营规模,典当大致可分为典、当、质、押四种。典的规模最大、资本最多、期限最长、利息最轻;当铺次之;质店又次之;押店最小,往往称为“小押店”,其资本最少,期限最短,利息最重。但是,都是以抵押方式提供信用,即出物质钱。
典当产生较早,但发展并不很快。明清时代随着商人资本的发展,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全国有当铺7695家,其中山西省有1281家,占16.6%;1724年(清雍正二年)全国有当铺9904家,其中山西省有2602家,占26.2%;1753年(清乾隆十八年)全国有当铺18075家,山西省有5175家,占28.6%。清末著名的银行家李宏龄说:“凡是中国的典当业,大半是山西人经理。”[2]19世纪50年代,在北京有当铺159家,其中山西人开办的当铺有109家,占68.55%。开设当铺的商人,“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3]咸丰中期,仅介休冀家一家所开当铺,今有铺名可考者十三家,即增盛当、广盛当、悦盛当、钟盛当、益盛当、恒盛当、文盛当、永盛当、星盛当、仁盛当、世盛当、鼎顺当、永顺当。还有许多当铺名不可考,大部分设在湖北樊城、襄阳、河北大名以及北京等地,相传有几十家之多。据《汾阳县志》载,光绪三年灾荒,汾阳各商号捐款名单中能够肯定是当铺者就有四十五家。由于山西商人经营稳健,所开当铺也就有不少为地方政府所利用。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山西巡抚明德上奏说:“查晋省当商颇多,也善营运,司库现存闲款,请动借八万两,交商以一分生息。五六年后,除归新旧帑本外,可存息本银七万余两,每年生息八千六百余两,足敷通省崐兵之用。”[4]山西当商与山西商品经营商人密切相连,多数当商和商品经营商人就是一个东家。当铺除了用月息一分到三分收息之外,还往往与粮商等其他商人结合进行投机,在秋收粮价下跌时,粮商以贱价收购粮食,典给当铺,取得质钱后再去买粮,随收随当,来年高价出售,当商粮商坐收厚利。至于当铺在戥秤上、银色上的高进低出,压平擦色,克扣贫民之事亦常有传闻。
印局
印局是放印子钱的商号。“印子钱者,晋人放债之名目也。”[5]这种信用机构的放款对象主要是城市贫民,也对小商贩提供信用。印局出现于明晚期,清初就已经很活跃了。到1853年(咸丰三年)内阁大学士、山西人祁隽藻在一份奏折中说:“窃闻京城内外,现有山西等省民人开设铺面,名曰印局,所有大小铺户及军民人等,俱向其借用钱文。”又说:“京师地方,五方杂处,商贾云集,各铺户籍资余利,买卖可以流通,军民偶有匮乏之意日用以资接济,是全赖印局的周转,实为不可少之事。”[6]由于太平天国革命暴动,印局止帐,“旗民无处通融,生机攸关,竭蹶者居多”[7]。这种借贷一般按日或者按月计息归还,多数是朝借夕还,也有十日或三十日归还的。每归还一次,盖一次印,故名印子钱。由于这种放款不要求抵押品,要答应说什么时侯归还,到期还款就可以了,所以也有人说叫“应子钱”。
印局除高利借贷外,还有一种剥削方式就是扣头,如借银700两,按“四扣三分行息”,即借款契约写700两,实际借款人拿到手的是280两,还得以700两借款月息三分付息,到期按本金700两另加利息归还。故当时有人写诗说:“利过三分怕犯科,巧将契券写多多,可怜剥削无锥地,忍气吞声可奈何?”[8]
印局与典当的区别,在于典当是以实物抵押提供信息,而印局则无需抵押,凭人信用;典当一般期限较长,三个月、半年以及一年以上,印局一般期限是一日、十日、三十日为限。投资印局的人和当铺一样,以山西商人经营者为多,北京、天津、汉口等地也都有这种信用机构。
帐局
帐局也称帐庄,是一种专门办理放贷取息的信用机构。投资帐局者,全国以山西商人为多,在山西商人之中以汾阳、平遥、太谷、祁县、榆次、徐沟等地商人为多。帐局获利方式主要是放款取息。其发生年代,大约在清雍正乾隆年间,可能与清政府的捐纳制度有一定联系,当然也是商人资本发展的产物。
最初帐局放款,主要对象是候选官吏。“遇选人借债者,必先讲扣头,如九扣,名曰一千,实九百也,以缺乏之远近,定扣头之多少,自八九至四五不等,甚至有倒二八扣者,扣之外,复加月利三分。以母权子,三月后子又生子也。滚利垒算,以数百金,未几累积至盈万。”[9]这种业务,称坐放官帐。候补官吏一到京,帐局就设法接近,发现其经济困难,就给予借贷支持。几年在京候选,时有招待送礼,交际应酬,一旦放以实官,制行装、买礼物,用款甚多,往往囊空金尽,只得向帐局借贷,帐局便趁机勒索,除抽收扣头,收取高利外,有时甚至扣押贷款人的证件或随行讨债。有诗道:“□帐西行鸷若鹰,深机□剥占层层,九成对扣三分利,尚勒穷员往任凭。”[10]帐局也放款给一般商人。“闻帐局自来借款,多以一年为期,五六月间各路货物到京,借者尤多。每逢到期,将本利全部措齐,送到局中,谓之本利见面。帐局看后,将利收起,令借者更换一券,仍将本银持归,每年如此。”[11]
帐局作为一种信用机构,从清初到民国初年存在了近三百年。一般资本都不大,大者十数万两,小者数千两,遍设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大江南北。还有在外蒙库伦、恰克图、以至俄国莫斯科等地设立者。如恒隆光、大升玉(茶庄兼帐庄),都与俄国商人有信用关系。1910年(宣统二年)因俄罗斯商人米德尔洋夫等五家商号倒闭,倒欠山西15家商人的620000余两白银案,引起国际诉讼,其中就有大升玉、恒隆光等帐局在内。根据现有资料,帐局的经营方式和业务活动,与印局区别不大,后来与钱庄的业务也逐渐趋于一致。似在清中期印局、帐局业务相类同,不少清代人认为他们是一回事。清末民初帐局与钱庄业务交叉,与钱庄业务类同。所以民国年间的山西商人自己并不把帐局与钱庄作严格区别,许多学者也认为都是“贷金业。”
山西帐局自清初至民国大体存在了300多年,在全国亦处于垄断地位。1853年北京有账局268家,其中山西商人开设的账局有210家,占78.35%。当时负责管理货币事务的户部右侍郎王茂荫说“账局帮伙不下万人。” [12]1904年北京设有“账庄商会”。
钱庄、银号
钱庄,也称钱铺、钱店、钱局、钱号、银号,由钱币兑换活动发生,最初是街市上的钱摊。由于明清时代社会周行的货币有铜钱、银块,零星小额交易需要钱文,大额交易一般需使银两,铜钱和银块之间兑换较多,多由殷实商号代为办理,随着商品交易的扩大,专门从事钱银兑换业务的钱摊便应用而生。在通衢闹市,设一木桌,按照市价,以银块制钱相交易,收取手续费,也称贴费。日久天长,又代客保存货币或临时借垫。营此业者,盈利颇厚,于是发展为店铺,设立铺面,业务范围也逐渐扩大,成为钱庄。有的则是商品买卖店铺兼营钱庄,后来放弃商品经营,专门从事钱业。这种演变从明代已经出现,但到清末市场上还有卖茶又兑钱,或卖烟又兑钱的小钱铺、钱摊、钱桌。
钱庄最初是从事钱币兑换业务的金融机构,后来业务扩展,也办理存款放款。山西商人在全国开设了多少钱庄,详不可考,据江苏工商业碑刻资料,1765年(清乾隆三十年),在苏州就有山西人开的钱庄81家。1853年(清咸丰三年),“山西祥字号钱铺,京师已开四十余座,俱有票存,彼此融通。”[13]据现有史料,北京、天津、张家口、归化、包头、西宁、兰州、河南、汉口等商业重镇的钱业势力多以山西商人势力为强。
随着钱庄家数的增多,各钱庄之间不能不发生一定联系,于是就产生了同业行会组织。归化城的钱业行会大约在乾隆年间就已经出现了。后来“各钱庄组合行社,名曰宝丰社。社内执事,号称总领,各钱商轮流担任。”[14]钱业行会如包头的“裕丰社”、归化的“宝丰社”等,作为所在城市的钱庄行会,承担着当地商业票据转账结算、银行清算、确定利率、组织货币市场、管理金融市场等职责。
票号
票号最初是专门从事异地款项汇兑的金融机构。票号的产生,一般认为是1823年的平遥日升昌,但是还有种说法,也需要重视,即为1679年(康熙十八年)太谷志成信是最早的票号。[15]山西票号的总号集中在山西平遥、祁县和太谷三县,分支机构散布全国及国外,总号分号统一核算。太谷帮先后有志成信、协成乾、会通远、世义信、锦生润、恒隆光、徐成德、大德玉、大德川等9家;祁县帮先后有大德通、大德恒、大盛川、存义公、三晋源、大德源、中兴和、巨兴隆、合盛元、兴泰魁、长盛川、聚兴隆、松盛长、长盛涌、公升庆、公合全、恒义隆、天德隆、裕源永、福成德等20余家;平遥帮先后有日升昌、蔚泰厚、蔚盛长、蔚丰厚、天成亨、蔚长厚、协同庆、协和信、协同信、百川通、汇源涌、永泰庆、宝丰隆、乾盛亨、其德昌、谦吉升、广泰兴、承光庆、日新中、广聚兴、三和源等22家。19世纪60年代南方商人介入票号领域,南帮先后有胡雪岩的阜康、胡通裕,云南的天顺祥、云丰泰,浙江严信厚的源丰润等几家,但是成立时间晚,倒闭时间早。可以完全肯定地说,在国内,从白山黑水到云贵高原,从东海之滨到北漠边疆,无处没有山西票号的分支机构。主要分号所在地有平遥、祁县、太谷、太原、介休、张兰、交城、文水、汾阳、忻州、大同、曲沃、解州、运城、寿阳、绛州、京师、天津、保定、通州、获鹿、张家口、归化、多伦、包头、喇嘛庙、库伦、恰克图、泊头、赤峰、沈阳、营口、锦州、东沟、吉林、安东、哈尔滨、汉中、西安、三原、盂县、道口、清化、禹州、开封、郑州、周家口、怀庆、赊旗镇、五河、济南、周村、烟台、青岛、南京、徐州、苏州、镇江、柏州、上海、青江浦、安庆、芜湖、蚌埠、正阳关、屯溪、杭州、宁波、福州、厦门、南京、九江、河口、广州、潮州、汕头、琼州、九龙、香港、梧州、桂林、南宁、湘潭、常德、长沙、武昌、汉口、沙市、宜昌、老河口、成都、重庆、万县、自流井、昆明、蒙自、贵阳、雅安、打箭炉、巴塘、里塘、拉萨、宁夏、肃州、甘州、凉州、兰州、迪化等500多处,国外的分支机构有日本的东京、大阪、横滨、神户,朝鲜的仁川,俄罗斯的彼得堡,印度的加尔各答和新加坡等地。在山西票号存续期间,由山西人开设的总号共43家,下辖分号共560家。[16]票号总号对分号实行的是集中管理,如果把总号比喻成大脑,各分号就是它的四肢。从分号的开立、经营、人员配置、资金、收益等都归总号管理,总号与分号、分号与分号之间,以“兹报、附报、行市、另起”[17]等方式互通信息,并采取“酬赢济虚、抽疲转快”的办法相互接济。正是这种灵活、严密而庞大的组织制度,使票号具备了“有聚散国家金融之权,而能使之川流不息”[18]的能力。
山西商人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扎根、发展,张家口上堡的日升昌巷,下堡的锦泉兴巷,分别是山西货币商人日升昌票号和锦泉兴钱庄建设并以自己的商号名字命名的街巷。外蒙古的科布多有一条大盛魁街,是山西巨商大盛魁建设的,这一切,如同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商人在伦敦、巴黎建设了伦巴第街,发展了伦巴第银行业务是一样的。根据19世纪下半叶的国内经济形势,1862年(同治元年)上海一地就有山西票号22家,对上海的钱庄放款达300多万两。1871年,又把自己的业务重心从长江流域的汉口,转移到了上海,1876年24家山西票号在上海成立了“山西汇业公所”,但在汉口的票号到1881年(清光绪七年)为止仍然有32家。在1883年的金融大危机中,上海78家钱庄关闭了68家,票号却未受损失。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在北京的票号对户部放款100万两。1904年“京师汇兑庄商会”成立。1906年汇兑公款2257万两。[19]
工具创新
山西银行的金融创新,可以与英国、意大利金钱商相媲美,某些方面超过了西方商人。在金融工具方面,在清初,山西货币商人已经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逐渐创造了许多信用工具。
一是凭贴,本铺出票,由本铺随时负责兑现,相当于现在的本票。
二是兑贴,也叫附贴,本铺出票,到另一铺兑取现银或制钱,相当于现在的支票。
三是上贴,有当铺上给钱铺的上贴,和钱铺上给当铺的上贴之分,彼此双方已有合同在先,负责兑付,相当于现在的银行汇票。
四是上票,非金融一般商号所出的凭贴称为上票,信用自然要差一些,钱商也可以接受,相当现在的商业汇票。
五是壶瓶贴,有些商号(包括钱庄)因逢年过节资金周转不灵,自出钱贴,盖以印记,用以搪塞债务,因其不能保证随时兑现,只能暂时“装入壶瓶,并无实用”,故称壶瓶贴,相当于现在的融通票据。
六是期贴,出票人企图多得一些收入,在易银时,开写迟日票据,到期时始能取钱,需计算期内利息,类似现代的远期汇票。
上述六种信用流通工具,最迟在道光中年已经在山西商人之中普遍行使。[20]前三种是见票即付现款,如同现金;后三种不一定立即付款,易生纠葛,道光皇帝曾下令准许行使前三种,禁止行使后三种,事实上禁而不止。
山西票号出现后,又创设了一些新的金融工具:
一是会券。会券也就是汇票,唐朝的飞钱具有汇票性质,明晚期异地款项汇兑的社会要求出现,为有分支机构的商号偶然代办,票据尚未规范。清代出现专营异地款项汇兑的金融机构票号以后,汇兑业务扩大,汇票制作、管理很快完善起来。有票汇、信汇,后来又有电汇。但采用最多的仍然是汇票形式。汇票按期限不同又分即票和期票两种,即票即见票即付,期票则是约期付款。
二是兑条。对小宗汇款,不用汇票,而是书一纸条,将其从中剪开,上半条给汇款人,由其转寄收款人,下半条寄交款的连号,相对领取,盖不用保。[21]
三是旅行支票。票号应异地贩运商人在沿途不同地点办货的需要,签发一种可以一次签发、分次在不同地方分支机构支取的汇票,类似现在的旅行支票或信用卡。假设由北京至苏州办货,可将一定数额的旅费交票号北京分号,开出一张汇票,当即说明途中经过济南、徐州、南京需要提取部分现银,到苏州后全部提出使用。北京分号即通知济南、徐州、南京分号(或联号),说明汇款人(提款人)的姓名,待提款人到济南后,可到指定分号提款若干,济南分号在提款人手执汇票上记录提款若干,下余若干。到徐州、南京也如此,直到苏州提毕,由苏州分号收回汇票。
二、业务、技术与制度创新
票据融资 无现交易
流动资金是企业经营活动中的血液,一般企业都会因为自有流动资金不足不能发展业务;同时,由于当时社会周使的是金属货币,白银与铜钱常常供应不足。晋商解决流动资金问题的办法,一是依靠信用贷货,二是依靠信用贷款。信用贷货就是商业信用(商品赊销),空口无凭,需要立约为证,创造了商业票据融资制度。信用贷款是晋商钱庄、账局、票号等金融机构对商号提供无抵押、一般亦无担保的贷款。晋商在其商业贸易活动中的资金周转大量使用商业票据与银行票据,现金收付较少。商业票据在使用中,还可以经过背书而流通转让,如光绪元年十月七日山西平遥蔚长永出具的一张票据,背书有34次之多,流通时间近一年[22],极大地解决了商品交易中的现金短缺的问题。下图是一张背书34次的流通汇票,左是正面,右是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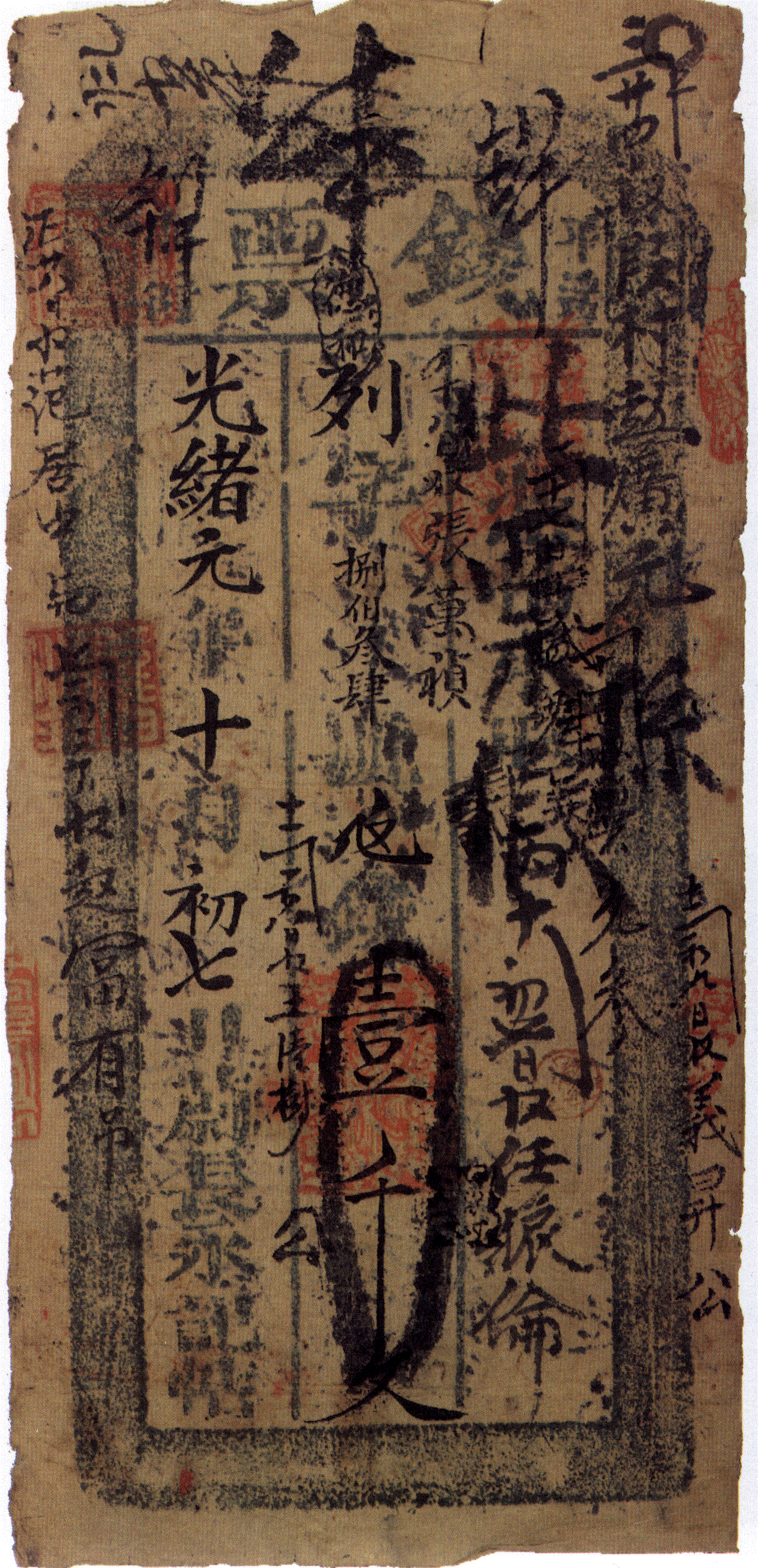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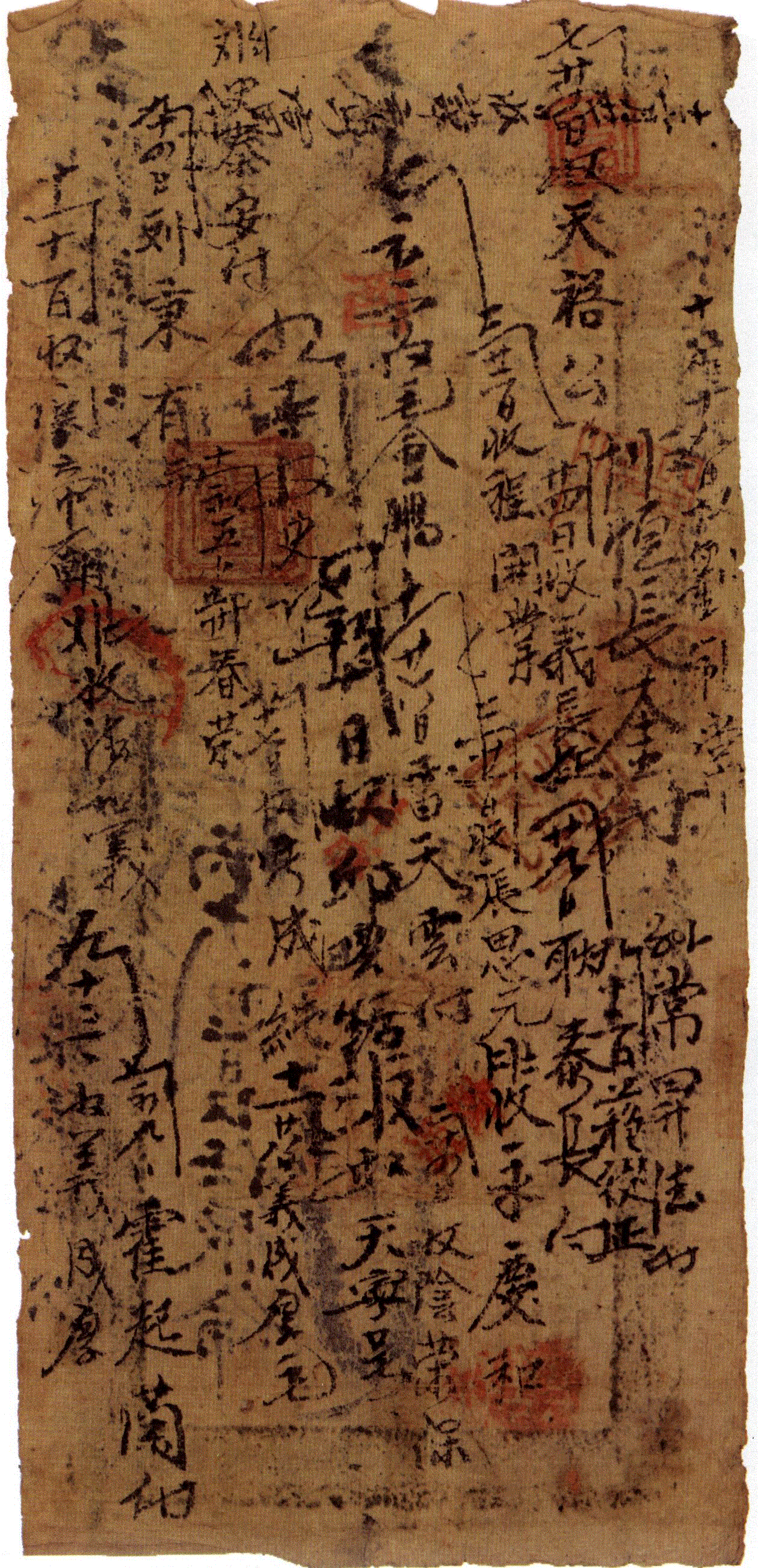
图片说明11 光绪元年十月七日平遥“蔚长永钱票”背书记录:“丙十月初七日收任振伦”、“十月十九日收刘佩常”、“十三(十月二十三日)恒长奎付”、“十一月初五日郝春荣”、“十一月十一日收关帝庙”、“十一月二十六日雷天云付”、“十一月二十八日义盛厚毛”“十二月初八日收王清树”、“十二月初九日收义升公”、“(十二月十七日)收永庆和”、“十二月二十一日收讳广富”、“正月二十八收范居中与”、“二月初六日收毛会鹏”、“二月初七日收霍起兰付”、“二月十一口光参”、“二月十四日收阴荣保”、“二月十七日盛魁口“、“二月二十九日耿长泰付”、“三月十九(三1文)收天宁号”、“三月二十一日收张思元”、“三月二十二日收程开业”、“三月二十四日段村赵广源”、“四月初一日收邱兴口”、“x(四月十七日)收德和义”、“四月十八日收张万顺”、“(五月十一日)常升德付”、“七月初二日收赵富有吊”、“七月二十四日收天裕公”、“九月十三日收义成厚”、“九月十四日刘秉有”、“九月十七日收张成纯”、“文 (九月十八日)史泰安付”、“九月口日收史记山”、“口月十四日收义长口”,共34条。 |
创立本平,全国通汇
清代各地白银成色不一,就是用来权衡银两的平砝亦不相同,官衡有库平、关平、漕平等,市衡是各地区不同,各行业不同,名目繁多,往往一个商埠就有几十种平砝。票号要实现异地汇兑,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平砝之间的差异问题。为此,各家票号都制定了自己的天平砝码,称为“本平”,与全国各地官方和市场通行的平砝确定折合比例,凭依通汇记账。本平制度的创立,不仅便利了票号的存放款和汇兑业务,而且使其总分号账务的记录及汇总有了一个统一的单位,使票号及时掌握其资产负债情况,并且使票号有了记账核算的货币单位。
创设密押 安全支付
为了异地款项汇兑的安全,使所用汇票真实无误而不发生假票伪票冒领款项,各家票号所用会票(汇票)都有自己的密押。
一是只能使用专用纸,即在总号统一印制的空白“会票”,纸质为麻纸,上印红格绿线,绘有复杂的图案或者周边雕刻蝇头小楷的五经四书的某些段落。
二是会票内加水印,如日升昌票号会票的水印为“昌”字,后来为“日升昌记”四字,蔚泰厚票号会票的水印为“蔚泰厚”三字。
三是各号书写会票,责定专人,用毛笔书写,其字迹在总号及各分号预留备案。各号收到汇票,与预留字迹核对无误,方能付款。
四是汇票书写完成,须加盖印鉴,现在看到的汇票盖有抬头章、押款章、落地章、骑缝章、套字章、防伪章等多枚印章。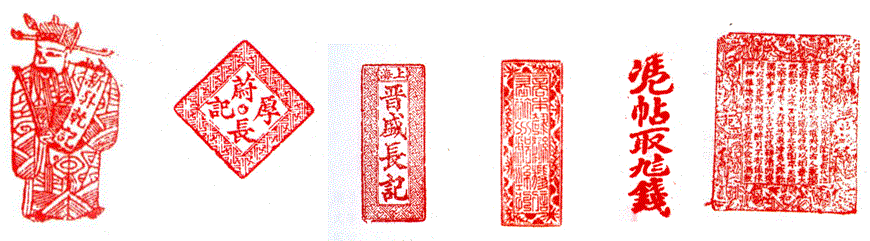
五是会票金额、汇款时间均设有暗号,有银数暗号、时间暗号,汇款人、持票人无法知道,只有票号内部专人才能辨认会票真假。暗号编成歌诀,以便记忆。如月暗号:“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十二字为一至十二月代号;日暗号:“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必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三十个字为初一到三十日代号;银数暗号:“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分别代表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国宝流通”分别代表万千百十。如“三月五日伍仟两”,即写“假薄璧宝”。为了万无一失,在暗号之外再加一道锁,叫自暗号:“盘查奸诈智,庶几保安宁”。[23]各票号密押不定期更换,新的代号均编成押韵口诀,号内有关人员必须死记硬背,烂在脑子里。
在具体办理款项支付时,又规定了安全措施,一般有三个办法:
一是讨保交付。票号为了保证款项安全支付,应商家要求,采取了“讨保交付”和“面生讨保”的办法。凡商家要求票号必须保证其汇款不遗失时,票号即在其汇票上盖有“讨保交付”的戳记。此种汇款,交付时必须取得商保。“面生讨保”则是在取款人生疏的情况下才要保人。
二是汇票挂失。对于遗失的汇票,视各地具体情况,采取了不同的应对办法。京师、保定多为“登报声明”,曰“日后此票复出,俱作废纸,不得为凭……特此布知”,“望中外绅商,切勿使用。”;汉口、重庆则通知当地分号料理,并报告当地政府、商会总会,同时照会驻当地各国领事。下面是1905年4月21日《大公报》一则公告:[24]
声明失票永作废纸启 因小号本年正月十二、十七两次由山东省城福兴润信局寄京信包迄今未到。查有天庆恒二月十二日期市平足银一千零四十八两四,永顺隆三月底期市平足银一千零四十八两四,又一宗四月半期市平足银一千零四十八两四,会票共三张,均在其内,该信局京号并不知情,而其山东人位全行逃走,以至无从根究,合即登报声明。日后此票复出,俱作废纸,不得为凭。诚恐华洋官商军民误为使用,特此布闻,伏望雅鉴。 京都新泰厚汇票庄顿启 |
三是出具甘结。在办理公款的汇兑上,尽管晋商一般相信官场不会有诈,但也不敢掉以轻心。为防万一,采取了领汇票要具甘结的措施,即除立汇票外,还要以票号名义与汇款人写下有汇款性质、数量、汇费等内容的字据。下面是源丰润票号福州分号与闽海关的一份甘结。[25]
具甘结号商源丰润今于与甘结遵依结得 |
转帐结算 银行轧差
中国的转帐结算与银行划拨清算起于何时?据《上海钱庄史料》,上海“钱业在1890年设立汇划总会,开始以公单方式计数,进行清算”[26]。其实在此之前,内地己有转帐结算与银行划拨清算方法,并且比较广泛地流行晋商创造的银钱拨兑和转帐结算,可以归化城的宝丰社为例。因为在这里的“银钱业商人,以山西祁(县)太(谷)帮为最,忻(州)帮次之,代(州)帮及(大)同帮又次之。故其一切组织,亦仿内地习惯办理,各钱商组合行社,名为宝丰社”。“宝丰社在有清一代,始终为商业金融之总汇,其能调剂各行商而运用不窘者,在现款、凭帖之外,大宗过付,有拨兑之一法。”[27]就是说自宝丰社成立以后,它就成了社会资金的总枢纽。当时“商市周行谱银由来已久,盖与拨兑之源流同。其初以汉人来此经商,至清中叶,渐臻繁荣。……边地银少用巨,乃因利乘便,规定谱银,各商经钱行往来拨账,借资周转,此谱银之所由勃兴也。其作用虽如货币而无实质。……拨兑行使情状亦与谱银相类,所不同者仅为代表制钱而已,市面通称为拨兑钱,即前之城钱也。周使惯例,数至一吊即可拨兑,吊以下使用现钱。各商均在钱行过帐,营业始能运用。”其时“钱行及各商行均可发行号帖,以资周使。”[28]一般是付款商号开出凭帖,相当于支票,持票人可以转帐,亦可以提现,现款限期在一月以内的又叫“点个儿现银”。假如商号甲无钱购货,经与钱庄乙商议,允许代理,商号甲便可以向商号丁购货,商号丁与钱庄丙有往来,钱庄乙便通知钱庄丙,声明商号甲已有存款,商号丁便可以放心地发货,无需现款,仅在甲、乙、丙、丁之间划拨转帐。但这种凭帖,只能相互间辗转划拨,不可提现,因为没有现金,晋商将此种办法称做“客兑银”。不过制钱拨兑,只能转帐,不能提现。由此可以肯定,在清代中期,晋商在蒙古地区已经按照内地办法使用了汇票、支票、本票,办理资金的划拨转帐和融通。可见内地的转账划拨时间更早。彼时银两转帐为谱拨银,铜制钱转帐为拨兑钱。
商户之间转帐结算的结果,形成各个钱庄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在钱行商会的组织下通过“订卯”结清,这是中国最早的银行清算制度。在规定时间,各钱商齐集钱业商会,“会同总领,举行总核对”,“如甲号以过拨结果存有乙号之款,乙号不愿存放,则提出另兑丙号收存,甲号如无实现指向,可以转拨别号,则本标骡期,营业立呈险象,本行均予拒绝往来。故钱行往往以出放过多而收项少致受亏折”。“订卯时互对帐目,或发现宗项错误,或虽经过帐,空无指项,则付出之款仍可收回,不生效力,俗谓之回帐。其应回帐之款,虽在过拨时辗转数号,甚或延期数年,亦可根据各号帐目逓予回销,此亦拨兑钱市特有之办法”。但是“如为面拨之项,则不能回帐”。银行间清算以白银十两或制钱十吊为起点。
山西银行间的清算有两种情况:一是系统内清算,如票号各地分支机构相互之间在一定时间内发生的汇差,我欠人,人欠我,以“月清年结”两种帐向总号报帐,月帐年帐均以“收汇”和“交汇”两项分列,既有细数,又有合计,均按与各分号和总号业务清列。总号收到报来的清帐,核对无误后,将月清收汇和交汇差额分别记入各分号与总号的往来帐,收大于交,差额为分号收存总号款项数;交大于收,差额为总号短欠分号款项数,互不计息。二是各金融机构在为企业办理转帐结算之后,形成金融机构之间的债券债务,规定定期“订卯”,相互冲销,差额清结。一般是按照标期进行。[29]
拆借市场 调剂头寸
银行同业的短期资金交易市场,与转账结算发生时间可能同时出现。《绥远通志稿》说,当时归化城货币商人的相互拆借、头寸调剂,“向例”在市口进行货币资金的交易。“每日清晨钱行商贩,集合于指定地点,不论以钱易银,以银易钱,均系现行市,逐日报告官厅备查,各钱行抽收牙佣,均遵章领有部颁牙帖、邀帖,……谓之钱市”。“为便利计,故有钱市之设,按市面之需要定银分及汇水之价格,自昔至今,一仍旧贯。”在这种钱市上融通短期资金的银钱业商人,因为大部分是山西人,故其一切组织,按照山西内地习惯办理。
这项工作的组织,由金融业行会负责。在归化城就是宝丰社。《绥远通志稿》记载:“清代归化城商贾有十二行,相传由都统丹津从山西北京招致而来,成立市面商业。……其时市面现银现钱充实流通,不穷于用,银钱两业遂占全市之重心,而操其计盈,总握其权,为百业周转之枢纽者,厥为宝丰社。社之组设起于何时,今无可考,在有清一代始终为商业金融之总汇。”由于钱市活跃,转账结算通行,宝丰社作为钱业之行会,“大有辅佐各商之力”。“平日行市松紧,各商号毫无把握,遇有银钱涨落,宝丰社具有独霸行市之权。”宝丰社可以组织钱商,商定市场规程,监督执行,如收缴沙钱,销毁不足价货币铸成铜碑,昭示商民不得以不足价货币行使市面,确保商民利益等,尽管没有垄断货币发行,代理财政款项收解,但它有类似“银行的银行”和管理金融行政的职能。
与归化城宝丰社同样性质的钱业行会,在包头叫裕丰社,在大同有恒丰社,等等。
镖局标期 信约公履
社会信用与合约的执行,即商品交易与金融交易中的债权债务的清偿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晋商在商品交易中大量运用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产生的大量债权债务关系,如何处理复杂的“三角债”,是晋商商会的重要任务。晋商在实践中创造了通过镖局、标期、标利制度,来实现各种经济信约的公履问题。 晋商商会根据镖局押运商品物质与现银的距离远近,决定各地标期时日,再按照标期的时间长短和标内标外的信用合约,决定利率高低,即标利。
标期有年标、季标(一年内分春标、夏标、秋标、冬标四标)、月标(亦称骡标)。商品交易中不论是信用放货,还是信用放款、介绍放款,其货款清偿和借贷,都按约定标期履行清债之责任,至标期到来也就是“过标”时而不能履行约定清偿的债务者,谓之“顶标”。债务人一经顶标,立地停止再借再赊,没有任何人与其交往,就可能成为这家商行倒闭的信号。按照春、夏、秋、冬四标归还欠款,在商界十分严格,不能超过一日,否则其经营顿归失败。但是居民住户,赊欠商家之账,则于标后逐渐清收,不以过标之日为严限。民户欠项,每到过标,多数先付半数,等到年终,才全部清偿。商人对住户之所以能够这样宽松,主要是由于商号采购办货付款期限较长,有较大的回旋余地,比如南茶北马和来自俄罗斯商品,多为年镖清结,有一些是隔一个两个镖期清结。所以,“苟使信用有素,购存货物,无须筹备现款,及期满应行归款,在营业周转一年或数标之内,已可以货易款,本利均回。此固尔时物力丰盈所致。”[30]
清末民初,山西省总商会设在太谷县,太谷是华北重要金融中心,各商家间的债权债务,多因批发交易而引起,决定了现银运送以及货款清偿、贷款归还大多集中于太谷进行。太谷周围各县,如太原府的祁县、榆次、徐沟、清源和汾州府的平遥、介休、汾阳、文水、交城各县的债权债务,批发贸易较少,多为零售交易引起,故太谷县虽然是太原府属,却是一个独立的标期,叫太谷标,各路运来的现银,在太谷集中并办理交收后,开出利率,然后其他各县以太谷为准过标、清算,并且形成各县的利率。周围各县均属太汾标(太原、汾州两府)。过标时,第一天清偿银两债务,第二天清偿制钱债权,第三天“订卯”,金融机构间轧差清算。不能按时履行信约,将不能获得信用。
标期来临,犹如“过关”,亦如“过节”,关系到所有商号资金供求和资产负债能否平衡,是企业兴衰存亡的关键时刻,晋商所有总号、分庄,无不重视。过标时由商会组织。当运载现银的标车外地到达,一般是在下午时分,夕阳西斜,明标到来(解现银者谓之“明标”),接近城门,便鸣火枪一声,赶车人高扬长鞭,人欢马叫,呼啸而入,络绎不已。商会组织所有商号和金融机构,筹措资金,聘请梨园优伶到城中的财神庙或关帝庙唱戏三天,娱乐庆贺,并祈求神灵保佑,发财致富,吉利平安。三天之内清偿债务,第一天清偿银两债务,第二天清偿制钱债务,第三天金融业各企业相互轧差清算,到此“过标”即算结束。
风险控制 机制创新
山西货币商人在金融企业风险控制方面,开创了中国历史甚至世界金融史上的范例。商人资本在经营活动中常常会遇到各种不同风险,发生亏赔倒帐问题,不仅会影响利润,甚至还会危及资本安全,货币商人更担心因信用危机而危及自已的存亡。为了防御风险,山西商人设计了多种防范机制。
首先是为了保证资本金的充足率,晋商金融机构实行本家族或者亲朋好友股份合作投资,资本金根据投资人的经济实力与意愿确定股份多少,作为股东,经营成果按照股份多寡承担风险和享有收益,创造了中国最早的股权融资制度。企业的成立,股东不直接经营,聘请可靠的有经营能力的人为大掌柜(总经理),授以经营管理企业的全权。股东与家属回避,建立完全的委托代理机制。金融企业的总号设在山西本地,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以致国外。实行统一制度、统一管理、统一核算,统一资金调度。总号对分号的考核,以“结利疲账定功过”,但以不对它号造成损失为原则,否则给予处罚。如山西票号总号先后43家,下辖分号共560家。[31]所有分号的开立、经营、人员配置、资金、收益等都归总号管理,总号与分号、分号与分号之间,以“正报、附报、行市、叙事报”等方式互通信息,并采取“酌赢济虚、抽疲转快”的办法相互接济。将企业内的管理层职工和业务骨干,按其职责、能力和贡献大小确定“人身股”多寡,作为人力资本,与财东的货币资本股一起参与利润分配,调动职员的积极性。资本金在企业成立时一次交足,每股多少两白银,各个人股份若干,订立合约,载入“万金账”,列为“正本”;另立“护本”,也叫“护本”或者“培股”,资金来源是在企业利润分红后,按股东股份比例(包括实物资本股和人身股),提取一部分红利留在企业参加周转使用,这部分资金仍归个人所有,只付给利息不分红,借以扩大经营中的流动资本,实质是建立风险基金,保证了票号的资本充足率。东家与顶有人身股的职员共同承担风险,东家是无限责任,承担亏赔全部风险,职员是承担有限责任,以所提副本为限。
一些票号原来的资本并不多,但由于提取“护本”较多,有时副本比正本还要多出几倍。如大德通票号在1884年(光绪十年)改组时,由在中堂、保和堂、保元堂、既翁堂、九德堂这5家股东投资,每股5000两,货币资本股20股,合计正本资本10万两,历年倍本情况是:1892年(光绪十八年)每股倍本1500两,共倍本30000两,正本副本共计13万两;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每股倍本500两,共倍本10000两,正本副本共计14万两;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每股倍本1000两,共倍本20000两,正本副本共计16万两;1904年(光绪三十年)每股倍本1000两,共倍本20000两,正本副本共计18万两;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每股倍本2000两,共倍本40000两,正本副本共计22万两,加上人力股倍本23650两,当时大德通票号实际资本达到25万两。[32]有的票号改组新增资本时,不仅需要加入正本,还要加入护本。1830年(光绪九年)天成亨票号改组,增资扩股,“将旧号之俸(股),归并入于新号,共作银股十俸”,新股每股5000两为1俸,“每俸随护本足纹银二千两……。至于人力,每俸亦随护身足纹银六百两。”[33]“护本”的名称比较多,有“获本”、“倍本”、“积金“、“备防”、“伙友护身”,还有的以另一堂名作为“统事”存入。日升昌票号的“统事”有200多万两,它是东家在大帐期所分红利未提,作为“统事”存放在号中的。以“统事”名义存入的资金,一旦发生亏赔,用于冲抵损失,如没有冲抵亏赔,其所得利息由东家与伙友共享,如果东家没有提取的红利不是存入“统事”而是号中普通存款,其存款利息归东家独享,伙友不得分肥。凡是进入票号的资本,不管哪种形式的资本,任何人不得抽走。晋商金融企业的资本金管理的副本设置,相当于国际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2007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新资本协议规定的经济性资本是一样,也比国际新定标准早了几百年。山西货币商人的风险控制办法与整个晋商企业的治理机制是基本一致的,在后面第四章晋商的企业管理部分将具体分析。
在业务经营战略方面,为了控制经营风险,票号坚持信用第一,慎于出票。业务与资金随经济社会需要而松紧。票号设置分支机构,先行调查研究,在掌握市场动向的基础上添置新号,扩展经营地域。如果不能经营,立刻撤庄。票号分支机构设遍通都大邑、商埠码头,如拉萨、巴塘、理塘、打箭炉、雅安等藏区虽然地理偏僻,却因财政和商务原因也设有分号。在太平军进军南京时,曾在长江一线太平军所到商埠收缩分号。因为日俄战争,营口业务困难,调整力量,设庄于朝鲜仁川,后又伸向日本神户、横滨、大阪、东京。分支机构设置随盈利与风险大小而伸缩。票号的业务经营,主要依靠自有资本,很少发行银行券,这一点与意大利金钱商相似,“慎于出票”。但是随着业务发展,不仅自己资金不足,也无法满足社会的货币需求。他们通过收受商业票据或者发行自己的短期银行票据,满足社会对交易媒介和支付手段的需要。
山西票号等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还有票据贴现,票号的汇票有即票和期票两种,对于未到期的汇票可以办理提前支取,但是需要交付一定的费用,相当于现在的票据贴现。还有代办业务,票号可以为商人代收货款,可以为政府代办捐纳、代办印结、代垫税款、代发股票、债券等等。还有“掉期”业务,19世纪80-90年代,货币市场和“汇兑行市”出现后,即因各地白银成色和平砝不同,付款地不同的汇票在交易中出现了价格差异,汇兑行市围绕两地白银的平价,根据银根松紧,在平价加减汇费的范围内浮动。“但在90年代上海、西安、桂林汇费支出大于汇费收入好几倍。”[34]票号业务中的“贴咱”、“贴伊”当是白银“掉期”业务。
还需要指出的是票号的顺汇与逆汇,顺汇是甲地先收汇款,乙地后付出。晋商票号实行联号制,各地分支机构在经营中往往出现此地现银多,彼地现银少。为了平衡现银布局,他们创造了“逆汇”办法调度现银。正常情况是:乙地动员吸收向甲地的汇款,在乙地收进现款,在甲地付出,此为顺汇。如果乙地现银不足,由乙地先贷款给当地企业,允其在甲地购货,甲地先付出、乙地后收进,此为逆汇,亦称“倒汇”。“中国此种汇兑,向所未有,至近年与外国通商,关系密切,内地市场间之贸易随之而盛,汇兑之种类不得不因之变化。……倒汇之手续亦别无烦累,……有信用之商人立一汇票,交于票号,票号即买取之,送交收汇地之支后,索取现金。”[35]逆汇的意义不仅仅是平衡现银布局,同时也是存放汇结合,能够扩大利润来源。如果是乙地分号先付款,甲地分号后收款,是汇兑与贷款结合。如果是乙地分号先收款,甲地分号后付款,是汇兑与存款结合。此种逆汇,不仅收取汇费,还计利息。这种财务创新,一是满足了商人异地采购急需款项的需求,二是减少了票号资金闲置,增加了利息收入,三是减少了异地现银运送,称作“酌盈济虚,抽疲转快”。[36]
三、为政府融资
清代后期,由于清政府财政恶化,捐纳筹饷是一项扩大财政收入的来源。山西票号抓住为政府融资的机遇,拓展自己的业务,步步深入,逐渐发展成为清王朝的财政支柱。
代办捐纳汇兑公款
票号最初是充当为清政府捐纳筹饷的办事机构。当时规定捐官人纳银,在省则交省库,在京则交户部,省库缴户部或其他用款地点,亦由票号办理,票号成了清政府财政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捐纳筹款的办事机构。
票号争取到了汇兑公款解缴税收的业务。本来公款上解,全系押运现银,主张由票号汇兑公款的理由是:(1)农民运动使道路不靖,汇兑比解现安全;(2)解现费用昂贵,汇兑相对费用低廉;(3)南省款项由水运上解经天津入京须支付海运保险费,保费大大超过汇兑时的汇水,又有海盗威胁;(4)地方税款所收银两成色大多不佳,不能上解,就地熔炼加工,又增开支,款项必有亏空;(5)由于地方税款往往不能按时收讫,常常不能准时起解,不得不向票号借贷,票号只同意借垫汇兑,不借现银,只得借垫汇兑。故咸同以后,装鞘解现日少,由票号汇兑日增。据不完全统计,从1865年到1893年,鲁、赣、湘、鄂、川、晋、浙、苏、皖、滇、黔各省及江海、粤海、闽海、浙海、瓯海、江汉、淮安各关通过票号汇兑公款达15870余万两,1862年为10万两,1893年扩大为525万两,32年增长到52倍半。[37]
借垫京饷协饷
票号为各省关借垫京饷协饷,解救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急。中央政府经费及各种专用款项,诸如“西征薪饷”(镇压西北回民起义的费用)、伊犁协饷、乌鲁木齐月饷、奉省捕盗经费等等,本由户部指派各省关将税款直解用款地点。但因各省关收入困难,用款单位则“急如星火”,各省关不得不向票号借款汇解。据部分清档统计,粤海关从1864年 (同治三年)到1890年 (光绪十六年)先后请协成乾、志成信、谦吉升、元丰玖、新泰厚借垫清廷指派“西征”军费,洋务经费等款项142万两。其他如闽海、浙海、淮安、太平各关与广东、福建、四川等省,均大量由票号借垫财政款项。光绪十年(1884年)福州将军兼闽海关负责人穆图善给皇帝的奏摺中所说:“历年所以无误饷款者,全赖各号商通挪汇解。”又如云南省历年镇压乌索、景东、开化、镇雄、宾川、邓川、宁州及腾越、顺之、永昌各处少数民族起义“紧急军需,刻不容缓,先后向各商号借用银39.81万两,填给库收,令付各省分拨归还。”“滇省库藏空虚,住特此商号二、三家(指天顺祥、云丰泰、乾盛亨票号)随时通融,稍免溃之忧。”[38]左宗棠说,从1866年 (同治五年)到1880年 (光绪六年)的十四年中,左军在湖北、上海、陕西向票号借款832.373万两,支付票号利息49.9591万两。[39]
表一:1865—1893年山西票号为部分省关汇款和垫汇情况[40]
省关 汇款总金额 其中垫汇金额 %
广东省 9,396,706 4,245,561 45.19
粤海关 6,607,553 4,539,947 68.71
福建省 8,552,202 3,521,645 41.18
闽海关 1,033,963 295,000 28.59
浙海关 125,781 50,000 39.75
淮安关 45,000 14,000 31.11
浙江省 2,197,591 230,000 10.47
筹借汇兑抵还外债
据清档有关资料记载,阜康票号财东胡光墉为清政府左宗棠军队镇压捻军和回民起义,向怡和洋行、丽如银行等外国商人借款,从同治六年(1867年)到光绪七年(1881年)先后六次,第一次120万两,第二次100万两,第三次300万两,第四次500万两,第五次175万两,第六次400万两,共计1595万两,均在上海办妥,由票号汇往山西运城或西安,转左宗棠军队提用。所借款项,以海关税作抵,仍由票号经办将各海关税收汇往上海外国银行还本付息。[41]
《马关条约》签订后,对日赔款2亿两,接着又增加赎辽费3,000万两,当时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尚不足8,900万两。为筹还赔款,被迫三次举借外债,第一次向俄、法借款4亿法郎,折合白银9,800余万两,第二次向英、德借款1,600万英镑,折合白银9,700余万两,均以海关税收担保,第三次是英德续借款1,600万英镑,因汇价变动,折合白银11,200余万两,以苏州、松沪、九江、浙东货厘及宜昌、鄂岸盐厘担保。四国借款每年计还本付息1,200万两,加上清政府的其他外国借款还本付息和开支,全国财政支出每年要增加2,000余万两。户部只得将每年所增开支,按省分摊,由各省筹款,不管是用盐斤加价还是地丁货厘附加等,必须按时将白银汇往上海还债,由几家票号包揽了各省债款汇兑:四川省由协同庆、天顺祥票号包揽,云南省由同庆丰、天顺祥包揽,广东省由协同庆票号包揽,广西省由百川通票号包揽,浙江省由杨源丰、源丰润票号包揽,安徽省由合盛元票号包揽,江西省由蔚盛长票号包揽,湖南省由乾盛亨、协同庆、蔚泰厚、百川通票号包揽,陕西省由协同庆票号包揽,福建省由蔚泰厚、源丰润票号包揽,河南省由蔚盛长、新泰厚、日升昌票号包揽,山西省由合盛元、蔚盛长、日升昌、协成乾票号包揽。
代理地方金库
票号代理财政金库,最初仅仅是少数省关,以后互相效尤,大多交由票号代理。当时《申报》评论说:“无论交库,交内务府、督抚委员起解,皆改现银为款票,到京之后,实银上兑或嫌不便,或银未备足,亦只以汇票交纳,几令商人掌库藏之盈亏矣。”[42]
票号直接为政府融通资金。据档案记载:“倭韩事起,征兵购械,需款浩繁。本年(1894年)八月间,当经臣部(户部)解派司员,向京城银号、票号借银一百万两,备充饷需”。[43]接着户部又要各省息借商款,解部备用,并订有《息借商款章程》,汉口日升昌票号曾为湖北省提供借款140万两。[44]广州源丰润也为政府提供借款10万两。[45]在江西,这种借款,“随收随交蔚长厚、天顺祥两汇票号汇数存储,另立清摺计数”,听候藩台文批,发交该二号汇解。[46]
为政府认购和推销“昭信股票”。1898年,清政府又以盐税担保,发行“昭信股票”,规定认购10两以上者给予奖励。清政府把办理股票推销业务的任务,交给了票号和几家满族人开办的钱庄。其中票号是百川通、新泰厚、志一堂(志成信)、存义公、永隆泰5家和恒和、恒典、恒利、恒源4家钱庄。当时在京城的48家票号,每家认购股票1万两,共计48万两。[47]由于流弊太多,社会抨击,被迫在同年停止了这种股票的发行。
庚子事变中,票号承办皇帝太后西逃财政事务。慈禧太后与光绪帝逃出北京,亡命西安,经太原时住山西巡抚衙门,慈禧宴请驻太原各票号经理,并请求借款。大德恒票号太原贾继英带头,慷慨应允借银四十万两,事后贾继英被召入京,赐穿黄马褂。
借垫汇解庚子赔款
1901年9月,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了卖国投降的《辛丑条约》,规定付给各国战争赔款白银45,000万两,年息四厘,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98,223万两。清政府为支付赔款,除从国家财政收入中腾挪出一部分款项外,其余则全部摊派各省,要求各省按年分月汇解上海集中,以便交付外国侵略者。庞大的赔款汇解、垫借汇兑,全部由票号承办,由驻上海的票号集中交付汇丰银行、德华银行、华俄道胜银行、法兰西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等外国在华银行,转往外国侵略者手中。
表二:1894年-1911年票号承汇各省关公款情况[48]
山东省 197,000两 江西省 5,586,509两
湖南省 4,583,686两 福建省 1,223,200两
广东省 17,633,782两 湖北省 8,114,672两
四川省 28,618,194两 山西省 3,217,926两
江苏省 2,184,156两 安徽省 8,724,364两
浙江省 16,545,569两 江海关 1,557,777两
粤海关 12,358,814两 江汉关 97,000两
闽海关 7,164,076两 浙海关 1,228,311两
淮安关 110,000两 蒙自关 133,599两
太平关 112,640两 瓯海关 40,000两
广西省 1,063,305两 云南省 202,664两
贵州省 463,372两 陕西省 4,838,788两
河南省 6,637,303两 甘肃省 4,518两
天津 220,246两 宜昌 38,000两
重庆 140,000两 营口 12,000两
芜湖 3,000两 河东道 426,863两
镇江关 102,085两 梧州关 30,000两
江宁 40,000两 宁 波 4,308两
杭州关 20,000两 奉省 12,314两
上海 432,485两
四、进入国际金融市场
购进国外货币金属
明清时期,中国的货币是白银与铜钱,但中国是贫银贫铜国家,晋商从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开始,每年两次用大型帆船从长江口出海,乘季风开往日本长崎,先后七八十年,为国家购进生铜约21000万斤,补充了铸造制钱的铜源。1821至1850年,晋商向俄输出商品,每年约在800万卢布上下,而俄国对华贸易的差额用白银工艺品“汉堡银”来支付,晋商将其铸成银元宝,投入国内市场。从17到18世纪,晋商在对外贸易中,吸收了大量西班牙、墨西哥银元,补充了国内白银货币。
开创国际贸易融资
晋商对俄罗斯商人的商品交易中,常常给予贸易融资便利,1899-1900(光绪二十五至二十六年),俄商米德尔洋夫等5家,欠晋商大泉玉、大升玉、独慎玉、兴泰隆、祥发永、碧光发、公和盛、万庆泰、公和浚、复源德、大珍玉、永玉和、广全泰、锦泰亨、永玉亨、天和兴等16家白银62万两,延抗不还。宣统二、三年晋商与俄商曾发生国际商务纠纷,库伦大臣上报外务部,照会俄领事。当时在恰克图、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巴尔纳乌、巴尔古今、比西克、上乌金斯克、聂尔庆斯克等地都有山西商人的活动。
走向国际市场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侵占我东北营口等地,合盛元票号营口分号业务停顿,濒临倒闭。总号18岁的年轻伙友申树楷立即走马上任,为营口分号掌柜。当时在战场危临下的营口人心惶惶,存者纷纷提取,贷者无法收回;人心浮动 社会骚乱,票号业务无法开展。申树楷业在调查中发现,日俄战后很多日本人来到东北,看中东北大豆及其制品,而中国人很喜欢日本的火柴、海味、杂货。他认为日本商人也是商人,可以直接与日商做买卖,说不定还可以使票号业务越做越大,越做越远。他大胆地突破晋商只用山西人的几百年老规矩,雇用一位日本人为合盛元的“跑街”,专门向日商招揽生意,业务局面很快打开,连对日做生意翻译问题也解决了。合盛元营口分号遂起死回生。稳住营口后,申树楷把视线移向全东北,先后在四平、哈尔滨、齐齐哈尔、黑河、丹东等地设立分支机构,特别看中丹东彼岸的朝鲜新义州,1898年在新义州设立代办所,1900年改为支号,并增设南奎山支号。总号大掌柜贺洪如看到申树楷的成功,遂想到洋人的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华俄道胜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接二连三涌入中国,山西票号与洋人银行营业性质相同,为什么不把票号设往东洋和南洋?更何况那里从事工商业的华人为数众多,留学欧日学生不下万人,因其无本国银行在外,利源外流,商务受困。便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冬)派申树楷率伙友若干,携巨款赶赴日本神户,几经周折,终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4月30日,在神户建起了中国在国外的第一家银行——“合盛元银行神户支店”。接着穿梭于横滨、东京、大阪等处,筹设合盛元银行出张所,四处呈文,又恳请中国驻日本领事及驻日朋友,在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间斡旋,耗时半年之久,终于在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冬,合盛元票号在日本东京、大阪、横滨、神户及朝鲜仁川等几处出张所先后成立。仅1907-1908年全年汇兑额都在2000万元以上。清廷王公大臣亦盛赞合盛元票号“开中国资本家竞争实业之先声,亟应优予提倡。”这是最早介入国际金融市场的中国商人。
五、对中国金融革命的贡献
如果说商业革命发生于明代,那么,金融革命则发生在清代,是商业革命带来了金融的革命性变化,山西货币商人为这一革命性变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土生土长的银行网络
当铺是最早的消费抵押放款机构,清代发展到高潮,1685年、1753年山西货币商人的当铺占分别占全国的16.6%和28.6%。19世纪50年代,北京的159家当铺中,山西人开办的当铺占68.55%。钱庄从事钱币兑换及存款放款。1765年苏州就有山西钱庄81家。1853年北京有山西钱庄40余家。[49]张家口、归化、包头等地钱庄基本为晋商垄断。印局是办理短期小额信用放款,无论京城还是蒙古草原都相当活跃。“京师地方,五方杂处,商贾云集,各铺籍资余利,买卖可以流通,军民偶有匮乏日用以资接济,是全赖印局的周转。”[50]账局从事放款,初期多服务穷儒寒士考取功名和捐纳,后转向工商业者,1853年北京有账局268家,山西商人账局有210家。票号为山西商人垄断,总号设在山西,分支机构遍布全国500多个城市,汇通天下。这些土生土长的中国式金融机构,它们创立记账货币,创新金融工具、金融业务、金融制度,遍布通都大邑商埠码头以致偏僻的藏区和远隔重洋的日本等地。它们是中国商业银行的先驱。
代替金属货币的票据流通
清代前期票据,在山西流通的有凭贴、兑贴、上贴、上票、壶瓶贴、期贴等,代替金属货币流通,曾经引起中央政府的关注,指示发展前三种,限制后三种。山西货币商人的会券(汇票)汇通天下,兑条、旅行支票为贩运贸易商人的异地资金支付大大提供了方便。晋商一方面用新的金融工具代替金属货币,节约流通中货币,同时有长时期的大量从国外购进货币金属白银与生铜,缓减了货币数量与商品流通的矛盾。
创立非现金清偿机制
清代金融机构逐渐开始为客户办理债权债务的非现金清偿,其办法:
一是拨兑。即转账结算,如内蒙古地区银两转账为“谱拨银”,铜制钱转账为“拨兑钱”。
二是订卯。金融机构为商户转账所形成的相互之间的债权债务的清偿问题,通过金融行会组织“订卯”,即票据交换,相互冲销,差额清结。
三是过标。晋商解决商品交易中赊销、借贷的债权债务清偿的社会约束问题,创立了镖局、标期与标利制度,通过商会组织的“过标”结清,社会信约公履约束。
企业化运作的山西银行
清代中国金融机构票号、钱庄、当铺、账局等山西银行,已经开始实行企业化管理,山西银行管理制度的特点:
一是企业股份制。几乎所有金融企业,都实行了多家共同参与的合作股份投资办法,这种办法有利于扩大企业规模,树立企业信誉,金融企业非此不能在公众中树立威信。
二是两权分离制。山西银行全部实行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制度,尽量摆脱家族成员的干预,让职业经理人更好地发挥作用。
三是总分支机构制。山西银行总号一般都设在山西本地,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以至国外,实行统一制度,统一指挥,统一管理,统一资金调度。
四是人身股制。企业内的管理层职工和业务骨干,按其职责、能力和贡献大小确定“人身股”,实行人力资本制度。
五是倍本制。山西银行的资本金分正本和副本,正本是投资人的货币资本,也叫老本。副本也叫倍本、护本,从股东和顶身股职员分红中提取留存企业,计息不分红,从而保证了资本金充足率。亏损时从护本中付出,无论如何不能亏煞老本。谓之“预提倒款,严防空底。”
六是银行密押制。为了保证异地汇款提款时的汇票真实无误,避免发生假票伪票冒领款项,票号创造了严密的密押制度。
七是金融稽核制。山西银行运用龙门帐进行财务稽核,可称中国早期的金融稽核,保证了财务核算的准确无误。
八是人力资源管理制。对新员工实行严格的推荐选拔制、三年学徒制、殷实商铺担保制、人力资本股份晋升制、行规号规的内控制,等等。
协调管理同业的金融行会
为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协调金融业内部及其与社会方面的利益关系,山西金融机构在一些大城市设立同业行会,如汉口的钱业公所、上海的“山西汇业公所”、北京“汇兑庄商会”、包头的“裕丰社”、归化的“宝丰社”等等。它们可以组织货币商人,商定市场规程,监督执行,如收缴沙钱,销毁不足价货币铸成铜碑,昭示商民不得以不足价货币行使市面,确保商民利益等,为本行的营业事项订定共同规则,组织金融市场运行,如汇兑平色、汇水、市场利率、票据交换、银行清算等,约束同业遵守,协调同行间的无序竞争;同时能够仲裁会员间的商务纠纷,协调会员与其他社会组织以及政府间的关系,维护共同利益。
六、山西票号的衰微
18世纪的中国,商业繁荣,手工业发达,贸易上经常保持巨额的顺差,但“天朝帝国”已呈落日的辉煌,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已经成为西方列强餐桌上的鱼肉。追其原因,欧洲商业革命,得益于文艺复兴运动,它带来了人性的解放和科学的崇尚,带来了民主和技术的进步,商人势力进入了社会主流。而中国的封建“皇权”制度和思想始终没有得以清算,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商人阶层没有登上社会主流地位,以山西货币商人为主的中国金融创业者虽然创造了骄人的辉煌,但是这一变革并没有导致工业社会的到来,显赫一时的山西银行过早地衰亡了,不能不说这是一场未能成功的革命,到了20世纪上半期,由江浙财团领头兴办起来的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艰难地承担了支持现代中国工商业发展的重任。这不能不说是山西银行的遗憾。造成这种遗憾的原因仍然是留给现代人的谜,似乎它也给了我们几点蒙胧想法。
根本位对票号的制约
票号业务技术建立在落后的银两货币基础上。1436年(正统元年),明政府解除“银禁”,法律上允许用白银作货币,从此确立了明清白银与铜制钱为本位货币的长达500年的历史。当时中国贸易出超,白银大量流入,加之政府库藏和银矿开采所得,白银来源充裕,甚至引起“银贱铜贵”。当时中国是全球经济大国,也是国际贸易的强国、顺差大国。在欧洲人建立了美洲殖民体系,用从美洲掠夺来的白银与亚洲贸易,换取以中国为主的亚洲产品,为了改变贸易中大量输出白银的不利地位,英国最先将殖民地孟加拉的鸦片转销中国,逆转了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优势,中国开始了长期的白银外流的历史。同时,从全球的视角来看,大洲贸易已经在海路贸易基础上形成大西洋三角体系,西欧拥有海航的商业与军事的优势,这种优势在金属本位货币的条件下,更直接地刺激了海上军事力量与贸易力量的结合,对亚洲的海上贸易的扩展,使原先带有易货贸易特征的中国与欧洲的陆路贸易冷落了。鸦片贸易的继续,引发了中国白银危机,直接瓦解了中国的白银货币基础。中国商业革命与金融革命正好是与白银货币相伴而行。不管中国国内银铜货币金属是“铜贵银贱”还是“银贵铜贱”,随着国际市场的形成,中国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世界市场的影响。18世纪中后期金本位制度在世界范围确立,中国却长期坚持银铜本位,而且不是银元本位,而是称量银两货币,这不能不给中国经济带来损失。中国落后的银两货币制度,严重影响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曾经商业繁荣、生产先进的中国没有产生工业革命的条件。落后的货币制度给商品经济造成的困难,也使山西货币商人的金融创新难以延续与发展。比如,银两货币制度在存、放、汇、兑中遇到平砝折合的困难,操作中自然存在压平擦色,很难促进社会储蓄转化为资本,办理转帐结算的存款银行也很难发挥货币创造功能,严重制约着经济金融的发展。
另一方面,从明清金银比价的变化,我们很难想象以白银为财富的中国与以黄金为财富的西方国家在经济交往中,中国商人的财富不会缩水。
金银比价的变化(单位:两)
年份 金: 银
1368(明洪武八年) 1 :4
1385(洪武十八年) 1 :5
1397(洪武三十年) 1 :5
1413(永乐十一年) 1 :7.5
1662-1795(康熙-乾隆) 1 :14.5
1796-1820(嘉庆年间) 1 :15.5
1830(道光十年) 1: 15
1850(道光三十年) 1 :16
1874(同治十三年) 1 :16
1885(光绪十一年) 1 :19
1888(光绪十四年) 1 :22
1893(光绪十九年) 1 :26
1894(光绪二十年) 1 :32
1897(光绪二十三年) 1 :34
1898(光绪二十四年) 1 :35
1902(光绪二十八年) 1 :39
1903(光绪二十九年) 1 :38
1908(光绪三十四年) 1 :38
1909(宣统元年) 1 :39
19世纪20年代,山西票号开张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创造“本平”,即当时异地款项汇兑业务因为各地银两平色不一,全国大体数千种平砝。票号自开始汇兑,就自设平砝,通过折合,统一各地平砝,有了货币记账单位,方使款项“汇通天下”。这本来是应当由政府通过货币立法解决的货币价格标准问题,政府没有解决,票号商人不得不通过金融创新克服这一困难。鸦片战争以后,国内外商品交易继续扩大,中国银两货币的价格标准问题,政府仍然没有关心,几十家票号各自设置本平,得益于汇款本平折算中暗中自有2-3‰的余平利益。然而开放的上海对货币制度的严重问题自然不能等待,1856年(咸丰六年),上海外国银行与商界公议,将往来账目一律改为以“规元”为标准,即以上海银炉所铸二七宝银折算使用,由公估局鉴定成色,合格者折算成纹银加以升水,支付时再以98%除之,所得之数就是上海通行银两的价格。[51]汉口开埠后,通行二四宝银,外国商人要求汉口商人依据上海规元折算的先例,以二四宝银980两升成洋银1000两的标准,即二四宝银的九八折扣,称为“洋例”。可以看出,鸦片战争以后的沿海沿江城市的外国商人与中国买办商人对中国货币价格标准的再一次创新,一直延续到1933年废两改元。这意味着票号商人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
三足鼎立变迁中的山西票号
当英国殖民者登上香港小岛,他们同中国人做买卖、谈生意的时候,第一关就是要丢开他所熟悉的英镑、先令和便士,去认识在银戥子上称银锭的本领。因而“英国政府的坚定意图是:香港的货币制度必须建立在英镑、先令和便士的英国体系之上。”[52]由于强大的中国习俗,英国政府终于在1862年同意香港殖民地单独使用银元,亦即法定的记账单位。汇丰银行的出现,是独立的香港货币体系最终完成的一个标志。汇丰银行1864年的注册执照中,特别规定有发行钞票的权力,1865年一开业,就立即发行以银元为单位的钞票。1867-1874年七年之中,汇丰银行的钞票由120万元上升到220万元,在华南一带广泛流通。之后的英商丽如银行、麦加利银行、有利银行也都发行银元钞票。“进入90年代以后,汇丰银行包揽了外国殖民地银行在中国的汇兑、存款和商业放款的绝大部分,包揽了发钞业务的绝大部分,还包揽了中国政府外债发行业务的绝大部分,以后又陆续包揽了中国关税和盐税的存放业务。也就是说,它在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市场以外,又进一步涉足中国财政和经济命脉的控制。”[53]
当外国银行还仅仅是在香港活动的时候,山西货币商人的势力已执中国金融之牛耳。未几就被另一种新的金融理念和制度逐渐替代,其演变的进程大体是:1863年以前山西票号独占中国金融的领先地位;1864—1893年,外商银行势力在大陆扩大,尤其在沿海、沿江开放商埠,形成了票号、外国银行、钱庄三足鼎立局面,票号的地位明显地在东南沿海的势力受到挑战。当时钱庄势力弱小,不过沿海沿江钱庄一般具有买办特点,与外国银行联系密切,可以找外国银行融资;同时与票号关系也很密切,也可以找票号融资。灵活应变的由洞庭商、宁波商发展起来的上海商人,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与洋人合作,甚至担任洋行买办,一边服务洋行,一边学习洋人,获得了许多新的经营管理技术。1894-1911年,民资银行在上海出现[54],上海钱庄与银行发展了汇划市场、证券市场,上海成为中外金融贸易的枢纽。他们有中西合璧之长。此时尽管票号在承办清政府对洋人赔款的汇兑上仍然占垄断地位,但是其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位实际上已经丧失。
在晋商与江浙财团势力的消长上,江浙财团之所以能够取代票号的地位,除了从竞争对手外国银行方面吸收了外来经验以外,主要还是票号内部问题,比如股东资本结构长期不变,对分得利润注重财富的保存,投向原籍土地与宅院建设或者窖藏,不注意资本性运用,没有增资扩股提高实力;不重视吸收小额储蓄存款,聚积社会资本,扩大贷款规模;贷款重人信用大于重物信用,在贷款无法收回时束手无策;在内部治理上,大掌柜全权独揽,没有董事会、监事会制约;实行股东无限责任制,破产清理时,债务累及东家家庭财产。同时,票号早期服务于以异地贩运贸易为主的商业资本,即商业金融,后期主要服务于政府金融,没有与工业资本结合。而20世纪上半期发展起来的江浙财团,与外国经济金融势力有斗争有合作,并且注意学习西方金融业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自己的业务主要服务于中国现代工商业。从事商业金融和政府金融的票号让位于新兴的江浙工业金融势力也是合乎逻辑的。
票号的异化
票号的产生与发展,本来是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发展,是服务商品贸易发展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本属商业金融。但是到清咸丰朝以后,其业务重心转向政府金融,承办捐纳报效清廷,借垫政府财政支出,成为清政府的财政支柱,使自己的性质发生了异化,把自己与政府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其资产很大一部分是政府的负债。辛亥革命清政府一倒,票号立刻就接二连三倒闭。
商业革命的成功必然伴随成功的金融革命。货币是金融运作的基本媒体,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货币与货币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政府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能依靠民间企业。当然作为经营、操作货币运行的金融机构,只有积极稳健地推进金融制度的改革创新,才能实现金融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市场的力量不能达到金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时候,政府就需要跟进,用行政的力量,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才能有助于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地发展。
[1]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德国柏林大学校长,地理学家,1868-1872七次在中国旅行,调查地质、地貌、矿产等等,著有《中国》三卷。
[2]严慎修:《晋商盛衰记》。
[3]李燧:《晋游日记》卷三。
[4]《清高宗实录》,乾隆二十一年。
[5]张焘:《都门杂记》。
[6]《祁隽藻奏稿》。
[7]《祁隽藻奏稿》。
[8]得硕亭:《草珠一串》。
[9]李遂:《晋游日记》。
[10]《日下新讴》
[11]清档:军机处《录附奏折》,咸丰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御史王茂荫奏折
[12]《祁隽藻奏稿》。
[13]清档:《朱批奏折》,咸丰三年四月初三日,《鸿胪寺卿祥泰为拟变通章程的奏折》。
[14]《绥远通志稿》卷四八,民国年间抄本。
[15]《晋商史料全览﹒晋中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29 页。
[16]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10月,第637—665页。
[17]《乔殿蛟访问记录》1961年1月,转移自《山西票号史料》第627页。兹报(有的叫正报), 它是做汇兑后,两个直接受教汇款好的一种营业报告;附报,是把各号每天的营业收交数字和码头全盘情况通告各分号以相互了解的报告;行市,是各号相互报告当地汇水、利息行市和“疲快”的交流情况的报告;另起(有的叫叙事报),是总号或分号对某分号的业务指示、评论及意见。
[18]王钰:《票庄纪略》,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第767页。
[19]《山西票号史料》第134-138页。
[20]《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30页。
[21]卫聚贤:《山西票号史》;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第692页。
[22]见王雪农、刘建民:《中国山西民间票帖》中华书局2001年第37页。
[23]山西财经学院、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94-695页。
[24]山西财经学院、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86页。
[25]山西财经学院、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89页。
[26]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3页。
[27]《绥远通志稿》卷四八,民国年间抄本。
[28]《绥远通志稿》卷三八民国抄本。
[29]《绥远通志稿》卷三八,民国年间未刊稿。
[30]《绥远通志稿》卷38(未刊稿)。
[31]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637—665页。
[32]卫聚贤:《山西票号史》重庆说文社1941年,第55-56页。
[33]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88页。
[34]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修订本第366页。
[35]《东方杂志》1917年第14卷。
[36] 颉尊三:《山西票号之构造》,山西财经学院、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票号史料》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68页。
[37]《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页。
[38]清档:军机处《录附奏摺》光绪二年,云南巡抚潘鼎新摺片。
[39]《左文襄公全集》卷四五、五四、五五、五九。
[40]《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4-138页。
[41]《左文襄公全集》卷二一、二九、四六、五O、五三、五八。
[42]《论官商相维道》,《申报》1883年12月3日。
[43]清档:户部档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户部复议侍郎寥寿恒议提各省公款归官借的奏摺》。
[44]清档:军机处《录附奏摺》,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湖北巡抚谭继洵摺片。
[45]清档:《朱批奏摺》光绪二十年□月□日,两广总督李翰章奏摺附片。
[46]清档:《朱批奏摺》,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江西巡抚法馨奏摺附片。
[47]《户部昭信股票章程》、《认领股票》,《申报》1898年4月13日。
[48]根据《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9-246页整理。
[49]清档《朱批奏折》咸丰三年四月三日。
[50]《祁隽藻奏稿》。
[51]中国银两货币的价格标准,有三次变化,一是1823年代初山西票号的“本平”,二是1856年上海的规元,三是1933年废两改元。
[52]转引自汪敬虞:《“同治银币”的历史意义》中国经济史论坛2004-3-3。
[53]汪敬虞:《“同治银币”的历史意义》中国经济史论坛2004-3-3。
[54]清末设立的商办银行有:1906年由周廷弼创办的信成银行,总行设于上海,是中国第一家商业兼储蓄业务的银行;1907年由浙江铁路公司发起组织的浙江兴业银行,主要为铁路股款的筹集和运用服务;1908年由李云书、朱葆三等人集资和办的四明银行,也是一家商业储蓄银行。